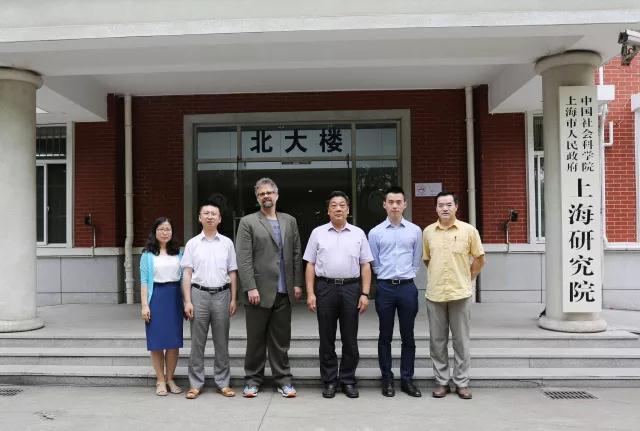6月28日,上海研究院“人文社科高端讲座”邀请英国巴斯大学的John Troyer教授作题为《关于生命、老龄化和人类死亡率的未来技术》的讲座,上海研究院合作处副处长李春光主持会议。John Troyer教授首先对英国巴斯大学死亡和社会中心进行了简单介绍:这是全球唯一一个研究有关死亡或者是葬礼以及人类老龄、人类死亡等诸多话题的机构。

技术战胜死亡的尝试
1979年,美国总统成立了最高的总统学术委员会、学术研究会,想搞清楚死亡的定义是什么。人们开始问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死亡,导致死亡的原因有哪些,这时人们开始重视生命,重视机器技术,看技术如何能够帮助到人。
在七十年代的时候研究的目标开始定位为大幅度地延长人的寿命。有本书写于六十年代,它的名字叫《未来不死》,Robert算是一个科学家,他在密歇根成立了人体冷冻法的研究学院,研究诸如人体冷冻法的课题。什么是人体冷冻法?就是先把人冻住,然后过一段时间把它解冷冻。
2018年,这项相关的研究已经演进到了更加高级的地步,有一个做这个研究比较著名的公司,运营方式就是它会把你的躯体放到大的试管中,承诺在你死之后,未来可能通过某种方法让你再重新回过来,至于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以后可能会出现把你的大脑从矮柜子里取出来放在计算机上或者是放在机器人的身体里的技术。
但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人类使用或者尝试用技术来打败死亡的一种的方法。假设300年之后这个大管子中人的躯体和矮柜子中的人的大脑重新活过来,周围你还认识谁,家人还在吗,你还能理解当时当地的文明吗?

死亡是否是禁忌?
1973年《拒绝死亡》一书问世,作者本身是人类学家,他引入死亡禁忌这样的概念。认为在西方死亡本身是一个禁忌,在整个社会语境下受到压抑,是不太被讨论的话题。我不太同意他在这本书中的论点,为什么?这本书的论点说死亡是一种禁忌,而我本人认为在人们谈论死亡、老去、临终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会感觉到不舒服,但是不能利用这本书中的“认为死亡是禁忌”这一点作为借口,不去深究或者是探讨死亡这件事。
如果死亡真的是一种禁忌的话,那今天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如果死亡真的是禁忌,大家肯定唯恐避之不及,又怎么会邀请我来这里,所以死亡本身并不是禁忌。其实每个国家的情况都有所不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措词或者话语体系讨论死亡这件事。
七十年代的时候,西方尤其是美国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死亡运动,还有社会团体讨论死亡本身,有什么样的运动?比如说自然死亡运动、死亡意识运动、有尊严的死亡运动,这些人整天不干别的,就是在讨论死亡,他们父母那一代的大学,1970年的时候首次引入了有关死亡、死亡的过程、与死亡相关的社会学、哲学等学科,那是大学第一次引入相关的学科教育,他们父母一代当时是既在大学里上了课程,同时也参与到社会团体的活动中。
那时候是1970年,而他们的父母现在处于别人的祖父母,现在正在经历老去的过程,所以现在注意力又重新回到死亡及死亡过程的讨论中,因为这其中也涉及到老龄化。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有很多电影或者书籍、新闻报道、游说团体或者是组织、讲座等活动,促使人们思考以及死亡的过程。
这些社会运动是想要做什么呢?是为了想要推进在法律或者是规范这方面有关死亡以及死亡整个过程的改变。事实上,七十年代有关死亡的运动是一种快乐死亡的运动,当时的人们是非常激动地讨论有关死亡的运动,他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
研究死亡问题的意义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呢?因为如果说你所爱的一个人,他根本心脏不跳动,只能通过机械生命支持装置维持生命,那这样的人到底是不是已经死掉了还是还活着?如果一个脑活动非常微弱,那这样的人是死亡还是处于生命的状态中呢?这些问题亟待我们回答。其实它也跟人类老去的过程息息相关,为什么?因为有些人是患了阿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症等病,这些人可能根本就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能够说这些人死掉了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并没有”。
围绕死亡展开的相关社会政治运动
在七十年代的时候,美国很多州也重新修订或者建立了相应的法律以赋予人们选择死亡的权利,举个例子来说1976年就推出了“自然死亡法令”,就是说作为一个公民你有法定的权利选择不再接受医疗救助,选择死亡。有了这样的法律背景的变化,到底未来学术的研究方向会有什么不同,和死亡相同的活动以及人们对于死亡谈论本身的兴趣是否会发生变化?其实并没有消失。
在美国,与死亡以及生命终结相关的事情也和政治有关,这是随着美国黑人运动而不断兴起,当时是涉及到有些黑人被警察射杀,他们由此发起了示威游行活动。除此之外,这类情况还在美国不同的形式呈现,2015年的美国最高法庭判决同性婚姻合法,这最开始牵涉两位男性的婚姻。这个大背景是这样的,这两个人结婚了,他们在马里兰州结婚,这个州同性婚姻是合法的,但是他们生活的俄亥俄州,同性婚姻是不受到法律认可的,是非法的。后来其中一个人得病死了,死亡后需要开死亡证明,证明这个人已经死了。在死亡证明书上,他的同性伴侣发起申请,想在死亡证明上标明是他的伴侣。申请被拒绝了,因为按照俄亥俄州的法律,两人并非处于婚姻状态。
这件事后来引发了最高法判定这种同性婚姻是合法的,这正是这种婚姻和死亡挂上勾的一种方式。当时说,我根本不要钱,我什么都不要,就是我想要我名字写在我丈夫的死亡证明之上。其实这样的一起事件促使美国最高法的判定并不是巧合,如果不让一个人把自己名字写在伴侣死亡证之上,这本身就不是公平公正的做法。
对于死亡的研究者来说,不可避免会捶击到一些更加宏观的社会问题,比如说会遇到法律方面的阻挠。
“协助死亡”的正当性
为什么在西方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趋势?因为在西方有些富裕的中产阶级,很多白人已经60岁或者是65岁以上,他们觉得自己是有权利决定如何赴死的。既然有这个权利,那我希望以合法、合适的方式去行使我的权利,而不想让州一级的政府告诉我这样是不合法的,他们想选用合法的方式完成。
在某些美国的州,比如说俄勒冈州,俄勒冈州处于美国的西海岸,它推出了一项法律“有尊严的死亡法律”,对于人的生命已经不超过六个月的人,他们可以找到医生说:“你给我开一个处方,我想要有尊严地死去”。但是有个前提条件,想要协助死亡的病人必须是自己有能力能够服用药,而不应该是医生开完药以后还要喂你服下,如果医生喂你服下药,那医生相当于犯了谋杀罪,那还是不合法的。
每年俄勒冈州都被要求公布一份报告,报告中需要包含两个事项,第一,发出多少个处方的药,第二,实际拿到药,并且也把药服下去人的死亡数量是多少。
其实就是说他们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选择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这其实恰恰代表着西方社会这些富裕的中产阶级思考死亡以及老去人的思想或者是行为方面的变化,这也恰恰代表着这种富裕的中产阶级和传统的州一级政府力量之间的纠纷或者是冲突,我觉得这种趋势最终会来到中国,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了,就是说中产阶级和政府力量之间的权衡。所以我认为最终随着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发展,这也会是一种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