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今中西”之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核心话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与发展的背景下,“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古今问题上,表现为保守性与现代性之争;在中西问题上,表现为民族性与世界性之分。未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应突破“古今中西之争”,尊重人类社会发展在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关联性原则,以一种公共性的情怀来对待“古今中西”的思想资源,怀着古今一律、中西共通的精神,在历史理性的指引下穿越“思想史三峡”。
历史学家唐德刚曾提出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类似于长江三峡,历经百折千回,终极奔流东去。他认为,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的建立与定型,要不断历经除旧布新、改进实践,需要两三百年时间,好比“三峡过尽,实验告终”,而在这期间,社会与民生都呈现一幅乱象。“历史三峡论”,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比喻,既正视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制度转型的艰难与曲折,也描绘了壮丽的发展前景,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我们认为,不惟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如此,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思想也是如此,也存在着一个“思想史”意义上的“三峡”。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与思想纠缠在古今中西之间,一会儿“中体西用”,一会儿“全盘西化”;一会儿“启蒙”,一会儿“复古”,其间发展曲折多变,但从长远看,也必将寻找到一条宽阔的河道,扬长东去,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将过万重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中国学术思想得到极大繁荣,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长足进步。但与此同时,在学术思想界,围绕“古今中西”问题的讨论从没停息过,依然处在上述 “思想史三峡”的一个历史阶段。思想学术的格局依然激荡在“古今中西”之间,甚至可以说是纠缠在“古今中西”之间。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学术与思想虽在曲折回环的“三峡”中穿行,但也必然会穿越这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奔流到更加宽广的历史长河中去。
一、中国思想史上的 “古今中西”问题
关于“古今中西”问题,直白来说,就是在思想文化转型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对待现代,如何对待中国、如何对待西方的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冯契先生曾经指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古今中西”问题,他说:“‘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那就是:怎样分析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批判继承自己的民族传统,以便会通中西,正确地回答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繁荣富强的道路。……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求正确处理古今中西的关系。可以说‘古今中西’之争贯串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今后若干年这个问题大概还是社会的中心问题。”冯契先生的这个论断,在其著述中经常提到,距今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应该说,最近几十年的思想史发展历程说明,这个论断依然是有效的。
其实,“古今中西”问题也不仅仅是近代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历程中也依然存在,在中国思想史上都充斥着“古今之争”与“华夷之辨”。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法先王、法后王的古今之争,也有华夷之辩。到了号称兼容的唐代,也有这样的争论,比如韩愈在批判佛教的言论中,就曾经呈现了中古时期中国的“古今中西”之争,韩愈对当时的佛道滥觞的思想局面十分不满,认为古时如何,当时又是如何,“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又将佛教称为“夷狄之法”,将其与“中国之教”对举并批判之。从韩愈的文字来看,对佛教以及当时思想界的批评与对本土儒家以及古代儒家思想的追溯之间的对比,实际上就是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的中古版。可见,“古今中西”之争,古已有之;只不过随着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开展,交通的便利、贸易的扩大,使得中国彻底卷入世界舞台,逐步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迈入现代化,故而,“古今中西”之争,于今为烈。
对于处在急剧转型背景下的中国社会来说,“古今中西”问题的实质在于:什么样的理想模式、好的范型是值得效仿和追求的?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寻找可供借鉴的理想模式、范型,这个模式究竟是按照传统儒家那样“言必称尧舜”,从古代思想中去寻找?还是近代以来很多思想家那样“言必称希腊”,从西方文明特别是近代以来首先出现在欧美国家的现代性价值中去寻找?在一定意义上,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古今中西”之争的要义之所在。“古今中西”问题,在古代表现古今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法先王”还是“法后王”。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则既有“古今”问题又有“中西”问题。如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里,论及理想社会的问题时,总会回到对上古先王之治的追溯上去,对于基于历史想象的“三代之治”“大同之世”,充满了精神上的向往,这成为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与文明的大规模传入,中国思想中对于理想社会的“型塑”又多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对象,特别是对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以及与之配套的政治发展模式,对于被“坚船利炮”震慑和困厄住了的中国思想家来说,更是充满了吸引力。因此,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界,在“古今”问题的基础上,又多了“中西”问题,概括而言就是“古今中西”。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中西”问题实质上也是“古今”问题。其中代表性之一的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观点,冯友兰先生曾经说:“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或现代底。……一般人心目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异。”冯友兰提出的这个思路,是将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的历史,有古代、近代、现代之分,而无地方性的差别。人类由于受地域和生产生活空间的限制,产生了不同形态的文明,但总体上来看,不同形态的文明中很多基本内容是相通的,也都是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发展。而且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化,人类文明的趋同化也在初现端倪。从世界历史的进程来看,冯友兰的观点无疑是有所见的。但是,我们这里,为了叙述的更加具体化和清晰化,我们还是以“古今中西”来具体说明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所处的大背景。
可见,“古今中西”之争时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命题,随着近代社会的急剧变革,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矛盾更为突出,故而这个问题更加急剧的凸显出来,成为时代思想的中心问题之一。由于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迅猛、民族性问题激荡,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彻底的解决,依然在当代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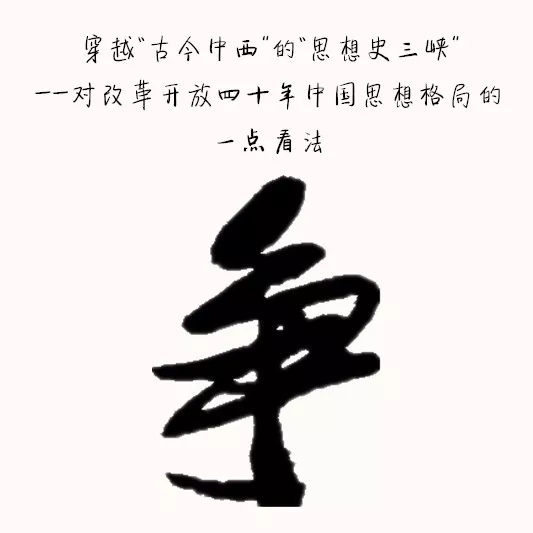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古今中西”之争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步、经济社会的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实质性进展,虽然政治体制既定,而且对于改革开放存在广泛的共识,但由于发展路径、思想资源的不同选择和认识的存在,由于政治立场、文化立场上的差异存续,因而对于何种思想文化更加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接续被中断了传统文化继续前行,还是接续新文化运动未竟全功的启蒙运动,是坚定的站在民族本位,还是拥抱所谓的“蓝色文明”,这些矛盾与冲突依然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呈现,故而“古今中西”的问题依然存在。
四十年前,中国重新回到屡被中断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建设,经济实现了腾飞,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民生得到极大改善,学术文化也实现了巨大的繁荣。在此同时,围绕“古今”“中西”的讨论却并没有因为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而稍有停息,而由于人们对现代化道路的不同认识以及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长期论争,这一争论显得更加深入。
关于“古今”问题,近四十年来呈现的是对现代性的追求与对传统文化的复归并存之局面。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力加速,为适应对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学术思想界在深入推动现代性的讨论,围绕着什么是现代性、何种现代性对于中国是恰当的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和讨论,期望以此推动全社会的现代转型,使得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运动,高举现代性的旗帜阐扬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等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在此基础上,延续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做法。当然,学术思想界也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兴起的思想背景下,他们认为“现代性”也同时带来了对于人的异化,有必要重新从中国传统中去发掘智慧。另一方面,出于对新文化运动以及“文革”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和做法的纠偏和否定,学术思想界又在极力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归,特别是自20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以来,国学、传统文化的回归呼声此起彼伏。在传统文化的复归中,政府、社会和学术思想界共同发力,已经初步形成传统文化全面复兴的局面:政府主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全面回归中小学教材,社会生活中传统因素增加,传统典籍的出版、媒体大力宣扬、传统节庆受到重视,等等,这些都显示了中国从急剧反传统的道路上转移到对传统的礼敬和接续的道路上。如所周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与传统文化的复归虽然不是简单的矛盾关系,但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与简单的复归传统文化,显然是有着巨大差距。特别是当前学术思想界和社会上很少一批人,强调传统中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应该加以弘扬的,不加鉴别分析的盲目“复古”,这些观念显然不能为接受了现代性洗礼的人们所能认同。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有两种情况值得警惕,一是依然采取某种简单、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对传统文化采取敌意的态度,一是有的人则一面享受现代化生活成果一面将脑子停留在古代社会,而这种两种现象都时有发生。概而言之,四十年来学术思想领域“古今之争”的局面,可以说是现代性与复古主义的矛盾,同时也夹杂着对现代性的反省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回归。
关于“中西”问题,近四十年来呈现的是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吸收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之挺立并存的局面。四十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是在整个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下、在向世界打开国门的形势下、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路径下开展的,因而思想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可以说,近四十年来,西方思想文化一直“在场”。当然,这种“在场”也一直伴随着中国思想文化的“争场”。一方面,中国学术思想界最大程度的学习、吸纳世界上(特别是欧美)优秀的学术思想。其主要表现是,欧美学术思想及其范式不断引进,欧美国家的学术思想理论、学术思想话题、学术范式、评价标准、话语体系不断进入中国;近四十年来,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和研究体制,完全是近代以来参照欧美国家的范式来建设的;同时,中国的学者也往往需要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知名高校“镀金”后才能进入中国高层次的学术单位,这些都是中国学术思想界对于“中西”问题的“行动”反应,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西化”的表现。另一方面,中国学术思想界也不断在强调学术思想的主体性,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强调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特别是近年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宣传和实际工作也正在切实推行,希望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话语体系之外,重建中国的学术思想话语体系,并将这一体系能够推行到欧美及世界其他国家。就这些现象而言,如果以简单的“中西”两立的立场来看,学术思想界往往会出现两种极端情况,有的人挟洋自重,一切简单地以“西方”作为判断和选择标准;有的人则以强烈抑或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态度,只要提到西方,就是“警惕”“反对”“遏制”等字样。这两种情况,无疑都将加重“中西”之间的对抗。四十年来的“中西”之争,除了意识形态领域之外,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就是西方的范式、话语、标准对于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改造,以及在此刺激下,中国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中自觉与自信意识不断增强。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虽然总体上人们能采取理性的态度看待“古今”和“中西”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古今中西”矛盾和问题也依然存在,非此即彼的现象时有发生,也依然还在“古今中西”的“思想史三峡”中穿行。我们认为,要穿越这一思想史三峡,就要以一种更加宏观的视野和宽广的格局来认识“古今中西”问题。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说,任何社会的发展,任何学术思想的进步,都不能割裂与前代的关系、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关系,任一社会形态之间都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关联性,因而思考与历史的关系、与其他思想资源、制度模式的关系,始终是学术思想发展的题中之义。晚近的一些学术巨擘就特别倡导打通古今中西来面对思想学术,比如,王国维就提倡“学无新旧、学无中西”,陈寅恪也认为自己做的是“不古不今”的学问,这些学术路线上的主张体现了宽广的学术格局。超越“古今中西”之争,其实质就是要尊重和强调学术思想领域的时间连续性与空间关联性,既强调传统的意义,也重视社会变迁的趋势,既强调本民族、本国的文化,也尊重外来的异质元素,从而在重视多样性思想资源和价值观念基础上实现综合创新,而不是去追问究竟是“古”还是“今”,是“中”还是“西”,“不论古今、无问西东”。
三、超越“古今中西”之争
如何更好的回应“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问题,跳出“非此即彼”的相对式思维,穿越“思想史三峡”?我们认为首要的是改变对于“古今中西”的对立式认识,而以一种公共性的情怀来面对不同的思想资源,将“古今中西”之异,看成是思想文化资源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将同一于滋养今天的思想文化发展历程,而非“厚古薄今”“厚今薄古”或者“抑西扬中”“抑中扬西”的极端道路。庄子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在世界上,事物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无法改变的,但是如何看待差异,是人力可以改变的,就像庄子在《齐物论》里所表达的思想,“客观之物”是不“齐”的,但人可以用“齐同”眼光来看待并以此消弭是非之论。具体到“古今中西”的差异性问题上来说,就是要避免在“古今中西”之间循环往复,有必要克服掉自身的分别心和“自以为是”的眼界,以一种“道通为一”的公共性情怀来看待“古今中西”。
第一,古今问题。在古今问题上,要坚持 “通古今之变”的原则,既不泥守传统,又在现实的基础上尊重和弘扬优秀传统,既不“以古薄今”又不“以今非古”,强调“古为今用”。具体来说,应该强调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古代的人或许并不逊于今人,但就类的意义上而言,现代社会总体上要优于前现代社会,因而要对中国社会持进步主义的立场。这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上,就是要根据时代变化,来选择思想和价值观念,而不是一味陷在复古主义的循环中。
清末以来,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覆巢之下,中国文化也同样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末的有识之士从器物、制度到文化层面对中国传统做了全面的反思,及至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领域形成了与传统文化做全面割断的激进判断。这种激进判断,导致了社会上一度出现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这种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性的认知之流风余韵至今未消。诚然,中国要走向现代,确实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深刻的反思,但是,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文化不是全面移植某种现代化、某种异质文化就能一蹴而就,而是应该生长在既有的传统之上。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无法回避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无法割断几千年传统对于现代及未来生活的深刻影响。传统文化构成现代文化的思想资源,当然,对于现代文化来说,这一资源既既有积极意义,有时也有消极意义。但实际上,对于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的举证,与对于传统文化消极意义的举证,将会是一样的多,纠缠于积极与消极的论辩,陷入庄子在《齐物论》中所说的若我互胜、莫辨是非的境地,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所面对的都是人类生活,无论古今,文化都是人类生活的创造物,在这一点上,古今是公共的。既然人类生活具有延续性,那么人类文化就具有延续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具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共同面对的是延续不断的人类生活,人类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一切因素,古人思考过,今人也要思考。就人性能力来说,古人和今日大致相同,因此,古今文化在面对共同问题时,其深度和广度往往不相上下。比如说,孟子要思考的“孺子入井”问题,今人也要同样面对“他者的痛”的问题,今天的伦理思考不见得比孟子的时代更为深入。因此,站在现代文化的立场上反思传统文化,要具有“古今一也”的公共情怀。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既要辩“异”,也要认“同”。
前文已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政府、学界和社会的共同推动下,人们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意义,一再宣扬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度对传统文化的损害巨大,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传统的割裂,从接续传统的意义上讲,当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无疑是及时的、必要的。然而,接续传统并不意味着彻头彻尾的复古,逢古必讲,逢古必好,逢古必宣,或者利用传统中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念为现代特殊利益集团“背书”,或者以某些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念来教导青少年学生,凡此种种,也是最近一些年来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内出现的现象,这就容易从彻底的“否定传统”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思想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复古主义”的坏处在于,对于时代变革带来的价值观念变革熟视无睹,而一味的强调固守传统,单个个体在生活中固守传统没有坏处,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但是如果借助政府权力、学校教育推行到公共生活领域,就会给公共生活带来价值错位、生活与观念脱节的紧张感,进而引发系列社会问题。质言之,弘扬传统文化具有必要性,但这不应该以对抗现代文明、现代性价值观念为前提,而应该在完成现代性启蒙的前提下来弘扬传统文化。正确认识“古今”关系非常重要,决不能简单的在古今之间做一“不相容的选言判断”,否则,中国的学术思想还将在“古今”之间的峡谷里来回穿行,跳不出历史的循环。
第二,中西问题。在中西问题上,要坚持“中西会通”的原则,避免简单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立场,重视世界其他国家的思想文化对于我们的借鉴意义。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故而,学术思想观念领域里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也越来越强烈。甚至已经有人要完全拒斥西方的学术思想体系,提出回到没有受到西学影响的文言文、理学、经学中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凸显中国的民族性和独立性。中国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学者,除了极个别的除外,大都能在坚持中国学术思想的主体性上形成共识,区别在于,究竟如何对待“西学”?
对于中西问题,也存在一个辩“异”和认“同”的选择。对于异质元素,我们要持一种宽容和平等的态度,要展现世界性眼光。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深刻影响,我们可以与西方思想进行对话,但完全不能忽视和盲目拒斥。就中国而言,无论是政治、经济、学术思想文化等领域,都能做到“中西会通”,最终达到“殊途同归”,无疑是理性解决“中西”问题的恰当思路。世界历史发展在不同地方的进度不同,故而表现出地域性的差别,然而,这种地域性的差异,不能被绝对化。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及认识自我、改造自我的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普遍性意义,不是哪个民族可以得而私之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不同民族的发展展现了不同的特色,然而这种差异不是本质上的差异,而是表现方式的差异。举例来说,中国人在对待家庭的态度上,具体说对于父母的态度,可能会与西方人有所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只是表现方式的不同,究其本质而言,只要是人,都要认真面对血亲伦理、血亲文明的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这一点上,人类是具有一致性的。从人类的一致性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表现各异,但是从根本上而言,所面对的问题具有公共性、共通性,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上所遇到的普遍问题,借用朱熹曾使用的佛教“月印万川”之喻,共同之月散在江河湖海,各处的江河湖海虽形态各异,但反映的是同一轮月亮。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时,我们往往过于强调中西之别,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实际上,中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背后,一样能找到人类共通的东西,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我们要以公共性情怀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关系,按照冯契先生的话,就是要参与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去,而不是关起门来“不睹不闻”。简单来说,对待“中西问题”,要具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普遍性意识。
就思想文化而言,四十年来的格局延续了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古今中西”的差异是事实性存在,我们不能无视这一事实。然而正视这一事实,不是为了人为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划界”,制造对立,延续斗争,而是应该从比较分析中批判扬弃、兼收并蓄,这才是一种合乎理性的态度。
四、小 结
在“古今中西”问题上,我们的总体立场上应该还是近代以来的进步主义,也可是说是启蒙的立场,同时也是辩证的态度,表现为对于传统中弊病的揭示,对于传统中进步因子的发挥,对于中国立场的坚守,对于西方优秀文明的借鉴。要在“古今中西”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明辨中西的传统,按照真理、正义的方向予以“公心”对待,借用冯契先生年轻时的话语,“退,则捡起中西的腐朽传统,扮起虚伪的面孔。进,则继承了古今的革命遗产,惟真理是从。”今天来看,如何对待“古今中西”,冯契的这些话语和思想虽然朴实,但依旧还具有鲜活的意义,远没有过时。
“古今中西”问题事关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不仅仅具有文化意义,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近代以来,由于在“古今中西”问题上形成观念的差异和偏执,引起了现实社会生活上的针锋相对,带来不少惨痛的教训,应该引以为戒。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的经济社会是伴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而迅速发展的,我们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得益于现代文明的进步和世界各国的交流。在学术思想领域里,虽然还存在古今之辩、中西之辩,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怀着古今一律、中西共通的精神,我们一定会超越这种无谓的争辩,在历史理性的指引下穿越“思想史三峡”。
(作者朱承系上海研究院研究员)
